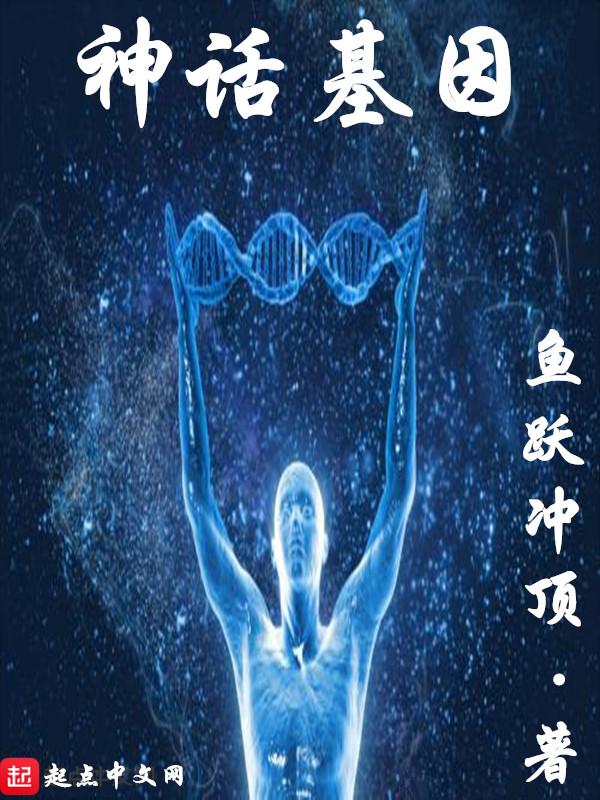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有人在夏天捡到猫 > 草莓(第3页)
草莓(第3页)
不出所料,烫得吓人。
多半是昨天淋雨的缘故。
刑不逾轻轻晃他,试图把人晃醒。非但没晃醒,岑溯哼哼唧唧一通,反而放开被子抱住他手臂。
刑不逾没辙了,小声问:“宝宝,你烧这么烫真的能睡着么?”
刑不逾很不想吵醒岑溯,但他更担心岑溯这样烧傻。
他强硬抽出胳膊,岑溯落了空,不怎么开心地睁眼掀他一眼,嘴唇微微撅着。
“你发烧了。”刑不逾很大方,完全不在意被起床气波及,好声好气地哄他:“把药吃了睡,好不好?”
不知道是不是发烧的缘故,岑溯眼睛湿润,嘴唇也红了不少。迷迷蒙蒙地看过来,着实让人心悸。
他乖顺应声。
大概是一个人住生病只能靠自己,岑溯家的药箱放在显眼的位置,刑不逾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退烧药。他找药前提早备了温水,方便岑溯能立刻喝。
回到卧室,岑溯不出他所料地闭着眼要睡回去。
刑不逾捏他下巴,迫使他张口。
“乖,先吃药。”
岑溯就着他的手喝水,少部分液体顺着嘴角淌下,被刑不逾擦干。
岑溯睡到日上三竿,烧不见退,刑不逾只好带他去医院。
岑溯软绵绵地趴在他身上:“不去医院,附近有家诊所。”
声音又哑又涩,活像在KTV唱了三天三夜不带休息。
刑不逾估计他扁桃体发炎了。
大夫给岑溯测过体温,又问了情况,开了药让输液。
小诊所空间不大,没放置几张床,全都睡着人,刑不逾没法,只好揽着岑溯,让他靠在自己身上。
要打青霉素,医生过来做皮试。揿针针头比留置针大,针头推进,刑不逾听到岑溯闷哼一声。
“做皮试,很快就好了。”
皮试没什么问题,医生拎来大大小小三瓶药。
药物作用,岑溯总睡不醒,刑不逾维持着揽他的姿势整整三小时。医生拔了针,刑不逾不忍心叫他,任他靠着多睡了会儿。
岑溯睁眼看到刑不逾清晰的下颌线,“唰”一下坐直了。
“睡饱了?”刑不逾按掉手机看他。
岑溯蒙着,呆呆点头。
下一秒刑不逾贴近,额头贴上他的额头,温凉的感觉停在皮肤表层,更炽热更躁动的情绪堵在岑溯心头。
这么近距离,刑不逾与他四目相对,鼻尖微微错开,像是要接吻。
岑溯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刑不逾好看的眼睛。
双眼皮,闭眼时眼褶舒展,看到一颗红色的小痣。
岑溯情不自禁闭了闭眼。
刑不逾轻哂,很快撤离,十分满意地说:“嗯,总算退烧了。”
岑溯心脏狂跳,压根听不清刑不逾在说什么,好像是说“送你回家。”
回家路上,岑溯一直攥着刑不逾衣角,闷头走路不吭声。
生病总会无限放大某些情绪,比如此时此刻的岑溯。
奶猫一样黏人。
刑不逾赶着回去,岑溯知道自己继续留人不合适,不情不愿松开手。
刑不逾看出他闹别扭,临走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,恨不能将人揉到自己身体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