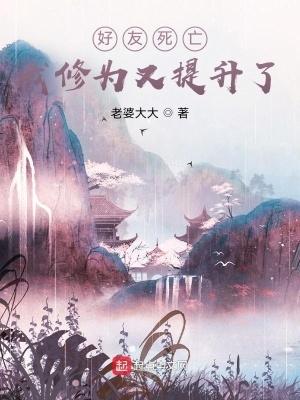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出宫前夜,疯批帝王后悔了 > 第466章 好日子在后头(第2页)
第466章 好日子在后头(第2页)
冬至前夕,山谷迎来一场罕见的大雪。积雪深达三尺,封住了进出山路。村中孩童无法前来读书,晚余便每日在屋中整理旧稿,将这些年所思所录编成一部《山居札记》。书中不谈权谋,不论朝政,只讲人心善恶、天地运行、耕读传家之道。
某日清晨,她在翻检箱笼时,意外发现一封未曾寄出的信。信封泛黄,墨迹犹存,竟是祁让的手书。
她怔住。
那是她出宫前三日,内侍悄悄塞入她妆匣的密函。当时她不敢拆看,怕动摇决心,便一直压在箱底,随她走遍天涯。
此刻窗外雪光映照,她终于缓缓启封。
信中仅寥寥数语:
>晚余:
>朕知你必去。
>这江山,本就不该困住你。
>六年共理朝政,你替我担尽风雨,而我……终究未能护你周全。
>若有来生,愿我不为帝王,你不为臣女,只做寻常夫妻,共煮一壶茶,同看一场雪。
>??祁让绝笔
泪水无声滑落,滴在信纸上,晕开了最后一个“笔”字。
她将信捧在胸口,闭目良久。外面风雪呼啸,竹屋簌簌作响,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那段错位的情缘哀鸣。
沈长安推门进来,见她神色异样,也不多问,只是默默接过信纸,读完后轻轻吹灭油灯,将她拥入怀中。
“他爱你。”他说。
“我知道。”她哽咽,“可爱得不够清醒。他把权力当作爱的方式,把掌控当成守护。所以他痛苦,我也痛苦。”
“而现在呢?”
“现在我才明白,真正的爱,是放手。”她睁开眼,望进他深邃的瞳孔,“就像你当年在太学廊下对我说的那句话??‘林姑娘,若你喜欢飞,我就做托起你的风。’”
他低头吻她额角:“我一直都在。”
除夕之夜,风雪初歇。村民们冒着严寒送来年货,有腊肉、米酒、手织棉布,还有一篮新鲜采摘的野梅。老人说,这是祖辈传下的规矩??每逢大雪封山,全村要齐聚梅岭,拜谢“白衣先生”与“素裙阿娘”的教化之恩。
晚余推辞不得,只得与沈长安一同接待乡亲。席间,一位白发老妪颤巍巍起身,从怀中取出一方绣帕,递给她:“先生,这是我孙女昨夜做的梦。她说梦见天上落下两颗星,化作男女二人,手持梅花,走入咱这山谷。从此旱涝不侵,五谷丰登。村里人都说,那是你们啊。”
晚余接过绣帕,只见上面歪歪扭扭绣着两人携手立于梅树下的身影,旁边题着一行小字:
**“愿仙人常驻,福泽千秋。”**
她眼眶湿润,郑重收下,回赠一本亲手抄写的《千字文》。
是夜,她与沈长安并肩立于山顶,俯瞰山谷灯火点点,宛如星河落地。
“你觉得,我们算不算神仙?”她笑问。
“凡人罢了。”他握紧她的手,“只是比别人多熬过了几场劫难,多守住了几份真心。”
正月初七,春风破雪而来。山径渐通,远方传来马蹄踏冰之声。这次来的不是朝廷使者,而是徐清盏,带着两名少年弟子。
“师父!师娘!”徐清盏翻身下马,拱手行礼,“弟子奉少主之令,扩建‘梅岭书院’。佑安帝拨银万两,梨月将军亲自督工,三个月内便可建成三进院落,可容百名学子就读。此外,江湖七十二寨共捐良田三百亩,作为学田供养师生。”
晚余惊讶:“建书院?为何突然……”
“因为您写的《山居札记》抄本已在民间流传。”徐清盏笑道,“不止百姓争相传阅,连西域商旅都带着它穿越沙漠。有人称您为‘南山先生’,说这部书足以媲美先秦诸子。”
沈长安闻言,忍不住笑了:“你又要当夫子了。”
晚余摇头:“我不是夫子,我只是个走过黑暗、终于看见光的人。我想告诉后来者:无论身处何境,都要相信光明存在。”
书院动工那天,阳光破云而出,洒在废墟之上。工匠们清理沈家祖宅残垣时,竟从地下挖出一口青铜古鼎,鼎腹铭文清晰可见:
**“忠贞传世,仁义立家。沈氏子孙,勿忘初心。”**
众人皆惊。唯有晚余平静地抚摸鼎身,低声道:“原来,你们一直都在等这一天。”
四月花开,书院落成。门前匾额由佑安亲笔题写:“梅岭书堂”。两侧楹联则是晚余所撰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