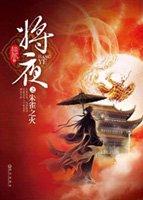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华娱:从神棍到大娱乐家 > 第五百七十九章 球状闪电中为雪糕加更(第1页)
第五百七十九章 球状闪电中为雪糕加更(第1页)
事实证明,从莫斯科去西伯利亚,并不比从国内去要近多少。
飞机降落在西伯利亚的冰原,寒风裹挟着雪粒扑面而来,瞬间将陈光和林云从莫斯科机场的喧嚣抛入一片白茫茫的寂静。
他们找到一辆破旧的出租车,司机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,帽檐压得很低,只能看到一副厚重的眼镜和紧抿的嘴唇。
车子在冰雪覆盖的公路上颠簸前行,窗外是无边无际的雪雾和黑压压的针叶林,仿佛永远没有尽头。
林云用略显生硬的俄语尝试与司机交谈,出乎意料的是,司机在瞥了一眼冻得瑟瑟发抖的陈光之后,突然切换成流利的英语。
“科学城……”司机声音低沉,带着一种学者般的腔调,“是上个时代浪漫主义的产物,当年的我们,天真地以为可以在这里创造一个新世界。”
他握着方向盘的手稳而有力,“可惜远离文明中心,人才不断流失,终究只是理想主义的泡沫。”
“您不像是个出租车司机。”陈光忍不住说道。
刚刚的俄语陈光没听懂,林云代为介绍:“这位是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研究员。”
“我研究的是远东未开发地区资源规划。”司机淡淡地补充,“一门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毫无用处的学问。”
“您……失业了?”陈光问道。
“今天是周日。”司机嘴角扯出一丝苦笑,“我开两天车,比一周工资还多。”
车内陷入沉默,只有引擎的轰鸣和风雪的呼啸。
车窗外,科学城的轮廓渐渐在雪雾中显现。那些五、六十年代的赫鲁晓夫楼整齐排列,斑驳的墙面积雪覆盖,偶尔能看到一尊被冰雪半埋的列宁雕像,指向某个已被遗忘的方向。
这座城市不像千年古城那样充满历史的厚重,却散发着一种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怀旧气息,仿佛一个刚刚逝去的青春时代。
车子最终停在一片几乎一模一样的五层住宅楼前。
“城里最便宜的住宅区。”司机在离开前摇下车窗,意味深长地留下最后一句话,“但住在这里的,可不是最便宜的人。”
陈光和林云面面相觑,继而推开沉重的单元门,一股陈旧的气味混合着消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。
门厅昏暗,墙皮剥落,只有几张模糊的政党竞选海报勉强辨认。他们借着打火机微弱的光亮,在狭窄的楼道里摸索,木质楼梯在脚下发出吱呀的呻吟,一直上到五楼。
刚绕过楼梯口,一个浑厚而略带沙哑的男声从黑暗中传来,用的是英语:“是你们吗?为BL来的?左手第三个门。”
他们推开门,瞬间被一种矛盾的感觉击中。
房间似乎很暗,但天花板上一盏裸露的灯泡又显得异常刺眼,浓烈的伏特加酒味和旧书纸张的气味混杂,环顾四周,书籍堆积如山,却乱中有序。一台老式电脑屏幕在他们进入时闪烁了一下,随即熄灭。
一个高大的身影从电脑前站起来。他胡须浓密,脸色苍白,年龄约莫五十多岁,眼神却异常锐利,仿佛能穿透人心。
“住久了,听脚步声就知道来的是生人。”亚历山大·格莫夫打量着来客,目光在他们年轻的脸庞上停留,“而能到这儿的生人,只有你们了,龙国人?”
陈光和林云点头,看着眼前由《飓风营救》的男主连姆·尼森饰演的俄罗斯老者,也是红色时代的科学家。
“我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去过那里,帮你们建三门峡水电站。”格莫夫顿了顿,语气带着一丝自嘲,“听说帮了倒忙?”
林云见多识广,她谨慎地回答:“当时似乎有这回事,泥沙淤积问题当时估计不足。”
“啊,又一个失败。”格莫夫喃喃道,像是说给来客听,又像是自言自语,“那个浪漫时代留给我们的,似乎只有失败的记忆。”
他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,然后再次深深地看了两人一眼,眼神复杂,低声说:“很年轻……你们还是值得救的。”
这话让陈光和林云心中一震,交换了一个惊疑不定的眼神。
陈光想到了那时候的张彬,跟自己说过同样的话。
格莫夫不再多言,将一个硕大的、装着浑浊私酿伏特加的玻璃瓶和几个茶杯大小的杯子重重放在桌上。他熟练地倒满三杯,透明的液体在昏暗灯光下泛着微光。
“我喝不了这么多。”陈光连忙摆手。
“那就让这姑娘替你。”格莫夫语气冷淡,不容置疑,随即将自己那杯一饮而尽,然后又倒满。
林云没有推辞,令陈光咋舌地端起硕大的杯子,仰头将烈酒灌了下去,动作干脆利落。
喝完后,她面不改色,伸手又将陈光那杯拿过去,喝掉了剩下的一半。
房间里只剩下倒酒和喝酒的声音,时间在伏特加的浓烈气味中缓慢流淌。
陈光看向林云,希望她切入正题,她却似乎被格莫夫的情绪感染,眼神变得有些空洞,只是默默地又灌下去半杯,然后直勾勾地望着前方斑驳的墙壁。
不知道是不是和之前在莫斯卡的哭泣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