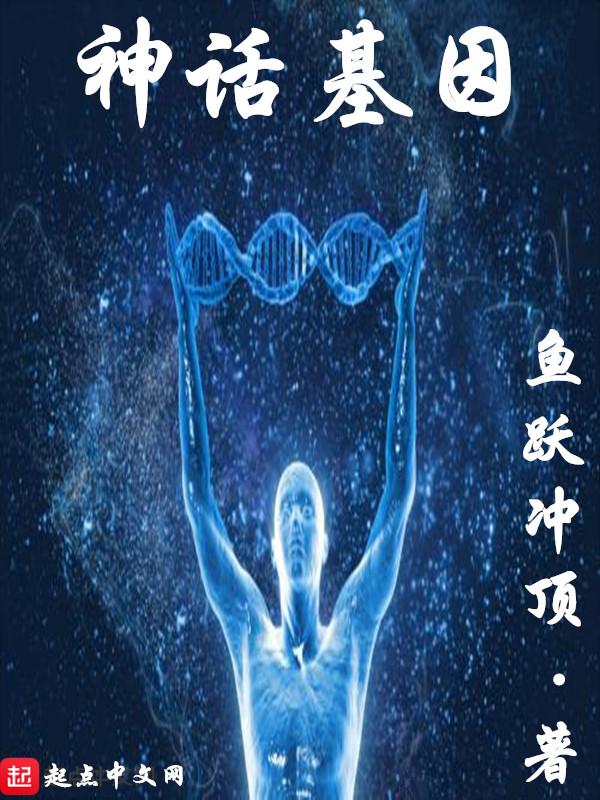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影帝他不想修罗场 > 19谈话(第1页)
19谈话(第1页)
夜色沉重,山道两侧的灯影被拉得极长,映在银灰色的车身上,如同流动的碎星。
傅宴容一手搭在方向盘上,指尖不轻不重地摩挲着缝线,半开的车窗透进山间微凉的风,拂过他微微低垂的眉眼。
江铭把车开到他旁边,杨婉坐在副驾驶,打开窗户笑眯眯地冲他打了个响指,说:“有家属在,今天江铭肯定赢啊,赌不赌?”
傅宴容偏过头,轻轻嗤笑一声,笑意未达眼底。
熟悉的人都看得出来他今晚有些烦闷,情绪如同山火未燃尽的余烬,只要风一吹,残存的火星就会漫过群山。
对讲机里传来低低的倒数声——
“三、二、一!”
油门瞬间一踩到底,轮胎与地面咬合的声音撕裂夜色,几辆车几乎同一时间弹射而出,尾灯交错,映亮了蜿蜒曲折的山道。
傅宴容的车居中,前方两辆车默契地相靠试图封锁他的路线,他眯了眯眼,指尖微收,方向微调,右脚精准地换挡提速,跑车瞬间窜出包围圈,银灰色的影子掠过夜色,犹如刀刃划开黑暗。
对讲机里传来此起彼伏的叫喊,他轻笑了下,没回应,目光仍沉稳地锁在前方。
山道陡峭,风声呼啸,护栏外是幽深的山谷,远处城市的灯光如碎金散落天幕,前方发卡弯逼近,傅宴容没有丝毫迟疑,手腕精准一拧,轮胎擦着路沿极限漂移,尾灯划出锋利的弧线,在惯性中漂亮落地。
后视镜里,江铭的车影被甩远了。
最后一条直道,终点近在眼前。
傅宴容不紧不慢地将马力加到最大,跑车引擎发出一声近乎嘶吼的怒吼,冲破夜色,带着不可阻挡的凌厉气势掠过终点线。
一片沉默后,身后的对讲机传来或赞或叹的笑声,以及杨婉不服气的抱怨。
傅宴容单手摘下手套,随意扔在副驾驶,紧接着靠进椅背,喉结微不可察地滚动,指尖按了按太阳穴。
心跳尚未完全平复,回忆却仍挥之不去。
空气里残留着汽油与高温摩擦的气息,窗外的风却是凉的,带着一点未散的雨意,渗进骨子里。
傅宴容之前喜欢赛车,是受了一部电影的影响。
电影的台词说,当赛车引擎到达7000转时,所有事情都逐渐褪色,机器变得轻若无物,在指尖消失,只剩下身体在时空中穿梭,七千转,一切美好始于此刻,你能感到它悄然来到你的耳边,让你扪心自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:“你是谁?”
六年前,傅宴容尚且需要通过这种极限的方式来把自我同其他碎片剥离,叩问自己的存在。
而现在,在穿过赛道终点线的那一刻,他竟然想起了之前在霁月岚庭的亭中,靠在他身边安安静静掉眼泪的宋临俞。
很多年前,他对宋临俞用一种玩笑似的语气承诺过:“哭对我有用。”
而现在,他只会平静地对宋临俞说:“你不要哭。”
傅宴容和他说自己有错,并不是出于安慰或者其他,而是因为他和宋临俞纠缠不清的开始确实源于他过分的自信和纵容,并且此后,他也仍然在袖手旁观。
车外有人拍了拍车门,傅宴容没动,只是静静阖了阖眼,打开车窗,懒洋洋地问:“什么事?”
“找你谈谈。”
来的人是江铭。
他这么说着,靠在傅宴容的车门上,垂下眼打量着车窗里的人。
夜色中,他冷不丁地开口,用有些好笑的语气对傅宴容说:“诶,你知不知道宋临俞一直特别讨厌我?”
傅宴容对这句话没做出什么反应,只是用一种接话的礼貌态度顺着问:“不知道,为什么?”
江铭耸了耸肩:“他觉得我拍戏的时候把你压榨得太狠,偶尔见面都要冷冰冰地剜我好几眼。你不在的这几年,他就差没像小说里写的那样,对我说一句‘天凉了,让江氏破产吧’这样的话了。”
听他说完,傅宴容摇了摇头,“江铭,你实在没有讲笑话的天分。”
“我没有开玩笑。”江铭这么说着,神色竟然显得有几分郑重:“你走之后,东钰给了我没办法拒绝的好处来做封口费,所以我连小婉都没说,毕竟,你和宋临俞之前的事越少人知道越好。”
“不过那天我还是很惊讶,因为是宋临俞亲自找的我,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没说什么话,直到最后要走了,他才回头对我说:‘江铭,我是真的很讨厌你。’”
讨厌他什么?
讨厌他在片场跋扈独断的导演风格,讨厌他总是因为一个镜头和傅宴容大吵一架……还是讨厌他见过16岁的傅宴容,讨厌他能成为和傅宴容谈天说地的朋友。
江铭停顿了片刻,似乎在回忆当时的情景。
“可是他说完之后,又对我道歉。”
那天,办公室里站了很多宋临俞的下属。他穿着一身冰冷的黑色西装站在人群之间,神色冷淡,语气锋利,看起来确实是一副天之骄子、高高在上的模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