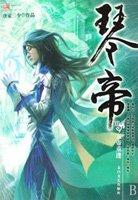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王妃与马奴 > 第103章(第2页)
第103章(第2页)
胆小的人,会事无巨细地设计这一场云雨,在青天白日里纵情任性吗?太子不相信她的说辞,她分明动心,也有为了快乐豁出去的冲劲。
「那日在琼山,孤便说过孤会说服父皇,也能让你顺顺利利地成为太子妃。话有些长,当日未来得及说完,本想过两日再慢慢同你解释的,结果你倒好,干净利索地跑出了京,都不给我解释的机会。」
越棠当日便不信他的话,今日也无动于衷,「殿下不必再在执着了,我问过爹爹与阿娘。。。。。。」
「孤出京前,曾拜访过右仆射。」太子忽然打断他,「孤向右仆射及夫人剖白心迹,已经得到他们的首肯了。」
越棠这才动容,他竟能说服爹爹与阿娘?她骇然问:「殿下别不是仗东宫权势压人,逼我周家上下就范吧?」
太子倒扬唇笑了笑,「这话若叫右仆射听见,只怕会恼你诬蔑他的人格。」
其实太子的计划,并不是什么出其不意的妙计,他将婚事当作一桩朝政,布局的乃是将来十数年乃至数代的朝局。
太子要立睿王的遗孀为太子妃,唯一的阻碍是礼法纲常。中书门下是第一道坎,外朝无人愿意拟诏,那这诏书便不必从中书门下走。
太子说:「先帝设翰林学士院,便是因不愿总受外朝掣肘,选亲信文士充知制诰,直接为帝王草诏,这便是所谓内朝。若再往前一步,在内廷设枢密史,诏书直接送至六部九寺,便可越过宰执,执行内廷诏令——孤上月便向父皇进言,枢密史如今已然履职了。」
第一道坎迈过去简单,至于令下后遭遇的百官口诛笔伐,这是第二道坎,便要多费些时日,非一日之功。
「百官也是人,他们在朝为官,为国为民,却也有家小要养育,总得为自己考虑。先前查鄞州之乱,正好给了孤一个契机,漕运丶河道丶船工丶盐铁,这些都要大刀阔斧地整改,而这些又是最耗费银钱的衙门。孤算过了,国朝明年岁铸三十万贯银钱,至少会有二十万贯投于此,若银钱流向的地方,皆是孤的亲信,你说还会有多少人闲得发荒,来管孤娶谁做太子妃?」
太子见她惊讶得说不出话,便知道她听进去了,欣然道:「当然不止于此,譬如世家子弟,坐拥家族累世兼并的土地丶广积的田产,朝廷那一二俸禄,并不很看得上,大约不那么容易被孤收买,可一旦漕运丶盐铁引都会悉数收回朝中,世族的钱粮命脉大大受挫,便不是那么回事儿了。何况国朝渐兴科举取士,寒门子弟虽还不能与世家分庭抗礼,但孤已请旨父皇,近年多加开恩科,新人替旧人,这总会是大势所趋。」
这第二道坎,不是一时之功,但桩桩样样已然铺开。鄞州之乱将往日朝廷脆弱的平衡撕开了道口子,在长公主的协助下,漕运丶河道上的积弊逐渐摊开,百废待兴,未来可期。
至于最后的身份问题,武皇曾于感业寺出家,杨妃以祈福之名得道士度牒,不外乎是借神佛之名,舍旧身得新生。太子觉得太和宫就很好,睿王妃去镀层金身,有了堂皇的幌子,大家面上过得去,也就行了。
太子看着她,轻声说:「一切新贵都会皇权的附庸,孤会成为国朝最有权势的太子,孤愿意娶谁便娶谁,那王妃,你愿意做孤的太子妃吗?」
第69章王妃是不是怕了?
九月初七是万寿节,这是整个秋日里最要紧的喜事。举朝休沐三日,天下诸州皆令宴乐同庆,到了正日子,在京五品及以上官员命妇皆入禁内,捧觞祝祷圣寿,间或还有外邦使节不远万里前来朝贺,延英殿前大陈歌舞,极尽喜庆欢腾之事。
越棠站在命妇堆儿里,仰望着张灯结彩的大殿,心道宫闱中的生活似乎也不枯燥,贵人们永远不缺作乐的点子。不出一月,宫中宴饮她都参加三回了,次次不重样,次次都有截然不同的美的体验。
群臣列着队伍诣阙颂寿,行三十三拜礼,完了由礼官牵引着退至两掖,便轮到命妇们上场。越棠站在头一排,边上是雍王妃与陈王妃,两位王妃年长她许多岁,大约觉得她无足轻重吧,都对她挺和气,从殿上退下后,陈王妃主动同她寒暄起来。
「听我家郡主说,王妃近来不在京中,回娘家养病去了,如今可大好了吗?」
陈王家的郡主?越棠思绪转了道弯儿,脑海中方才浮现出河间郡主的脸。
(。)
:|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