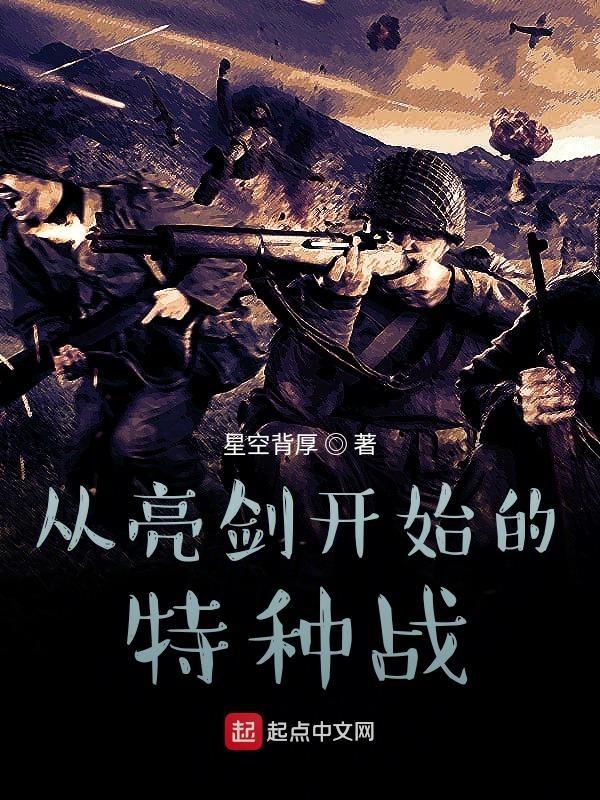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吾弟大秦第一纨绔 > 第492章 吕叔你相信我嘛(第1页)
第492章 吕叔你相信我嘛(第1页)
在张苍若有所思的眼神下。在浮丘伯、陆贾、毛亨敬佩高尚品格,不畏强权的眼神下。李斯高昂着头,像是一只高傲的大公鸡,跟在嬴成蟜的身后,没有一星半点的臣下感觉。嬴成蟜随意找了一间居室进入,看了一眼厅堂里张望着的四人,对随后进入的李斯加重语气说道:“关上门。”失去官职,爵位的李斯只迈进房中一步,就站在门前不再进去,靠在房门上,声音洪亮。“事无不可对人言。”正要做下的秦二世怒起,一巴掌拍在桌案上响声清脆。“你就是如此对待你的君王乎?”李斯不卑不亢,说出来的话和他那张脸一样刻板,就像是定了法令。“君之视臣如手足,则臣视君如腹心。“君之视臣如犬马,则臣视君如国人。“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雠。“陛下夺斯爵,除斯官,流放斯至瀚海。“如此行径连土芥都不如,陛下想要斯如何对待你呢?斯之所以没有拿着盾牌,提着刀剑行刺。是恐家师不喜,非不愿,不能也!”嬴成蟜抓起桌案上摆放的茶盏,用力砸了过去,正中李斯额头,头破血流。“要不是看在荀子的面上,你当朕会放你出咸阳狱!让你再一次当面激怒朕乎!”愤怒的嬴成蟜就像是一头狮子,咆哮的声音让看到李斯被打,想要过来说和的四大弟子驻足不动。鲜血从李斯额头流到脸上,又滴在了衣襟上面,凄惨又狼狈。但他高昂的头颅依旧是不愿低下,反而比之前昂的更高了些。嬴成蟜怒极反笑,大喝一声,叫来随行郎官将李斯带去太医署求医。李斯不走,被两个郎官硬架着出了门。怒气冲冲的嬴成蟜出了长安君府,上了驷马王车,隔着一个车帘对车辕上的章邯道:“看好李斯,别让他死,要夏无且亲自诊治,朕不希望明日听到一茶盏砸死一个人的事。想利用朕,踩着朕名留青史,做梦!”“唯!”连夜被送到咸阳宫,带到太医署的李斯没有死。在医家传人夏无且的手中,死也不是一件容易事,何况只是看着吓人的皮外伤。人没死,自然也没有一茶盏砸死一个人的故事流传。但有别的故事流传。送往咸阳宫的这一路,被郎官押送的李斯如同囚车游行的囚犯一样在咸阳路上转,脸上,衣襟都满是鲜血的狼狈模样,被许多人看见了。李斯刚正不阿怒斥陛下,陛下愤而掷盏的故事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,李斯的清名开始在各个世家推波助澜下在关中传开。他们不敢直接对抗秦二世,但敢将秦二世反感的人树立成一个典型。这样的小事在当下看似乎没什么用,但就是这样一个个没用的小事,累积在一起才能成为足以颠覆皇帝的大事。如果想压死骆驼,就要最后一根稻草到来之前,提前准备好数不清的稻草。一个车队自咸阳北城门出,向着西北进发,一百个车队护卫尽是披坚执锐的甲士。这是押送以李斯为首的五个秦臣,去往瀚海的车队。秦二世为表大度,无谋害这五位奸臣之心,特意从军中拨了一名百夫长,带百名秦兵,保护这五个秦臣安全抵达瀚海。不是被如同狗一样牵着走路,而是坐马车而行。这是自秦非子受封秦国以来,秦国流放犯的最高待遇。没有人以为这是秦二世心善。流放就是流放,还是流放到不是秦土的瀚海,结果必然是个死,怎么去,很重要?坐着马车很舒服,但知道是去送死,这一路身体无碍的行程,内心难道不是最大的煎熬?车厢内,蔡妍看着额头上有一道新鲜血痕的夫君,恨恨咬牙。“我要咒死这个昏君!”李斯听着车轮压在地上的声响,摸了一下额头手伤部位,感到有些疼痛的他却露出一丝笑意。“不可对陛下不敬,陛下是在成全我。”蔡妍一脸不解,除官夺爵,流放瀚海,打破你的头,这是成全?自家夫君是被打蠢了嘛?“你若相信斯,就别问了。“要不了几年,斯会带你们重回咸阳城,斯的爵位和官职会比现在还要高。”蔡妍靠在李斯怀中。“我自是相信夫君的,天涯海角,都随夫君走便是了。只是瀚海苦寒,恐我们那几个孩儿受不住……”听着细君担忧哀伤的言语,李斯脑中想的能要一个不识字的女人一年间能言语成文,简体字,真是可怖。搭配上活字印刷术和纸张,两年韩地学堂培养的官吏数量,足可媲美韩地二十年士子之数。“安心,我们不会到瀚海。”相邦府后堂,除了姜商以外,所有人都被清了出去,包括左丞相周青臣,右丞相冯去疾。相邦府的人早就习惯了。自传国玉玺秘密运到相邦府,自章台宫从秦王理政之地变成荒淫宫殿,相邦府后堂就成为了大秦帝国最高政务地。,!勤勉的秦二世这个月已经是第二回来了。刚为左丞相的周青臣羡慕地向内张望,他真的很羡慕被单独留下,为陛下最为信任的相邦姜商。他记得先王在时,陛下曾在朝堂上招募他,希望他能成为其府上门客。若是当初他答应了,那么现在后堂中就应该有他一席之地。“李斯走了?”被周青臣实名羡慕的吕不韦放下手上奏章,轻声相询。嬴成蟜点点头。“走了。”“他是个聪明人,看出了你要做什么,不想陪着你遗臭万年。”“是啊,他真的很聪明。”嬴成蟜笑了笑。“人前人后,口风都是滴水不漏,吕叔从前说他是和你一样的商人,还说他是赌徒,如今看来,是走了眼咯。”“用和你这两年的情意,换了一次流放。赌你这个人念旧,不会杀人,老夫看人除了你看不实在,就从没出过错。”嬴成蟜竖起大拇指,敷衍道:“是是是,吕叔最厉害了。那吕叔猜猜,李斯是要去扶苏那里,还是将闾那里。”“上郡。他这个人,不会满足于虚名的,今日丢下的一切实利,来日都会加倍找回来。”吕不韦一边说,一边从叠的整整齐齐的奏章中抽出一张递给嬴成蟜。“李斯这一走,闹出来这么大动静,也是帮了你分化的忙。朝堂已然初步稳定,你不能再懒散下去了,看看这张武城侯奏表。”嬴成蟜顺手接过。“皇兄做皇帝的时候,你什么都不让他干,独揽大权。我做皇帝了,让你独揽大权你还不干了,非要我理政。“吕叔啊,我就想像阿父一样轻轻松松,做一个甩手的王,你就勤勉一些罢,大印都在你手上呢。”吕不韦不理,不回应。嬴成蟜耸耸肩,只好聚精会神看起了奏章。不到一盏茶时间,嬴成蟜就看完了,笑容更浓郁了。这封奏章开头先是贺新君登基,然后说了会稽郡郡守殷通意欲谋反已被诛杀,封地多在会稽郡的尉缭似也有不轨之心,请领兵诛之。“你还笑得出来?”“当然笑得出来。我都做好王翦起兵造反的准备了,结果这位武城侯竟主动要带兵平乱,真是意外之喜。”“齐地遥远,具体情形犹未可知,焉知不是王翦意欲谋反,而殷通发现其不臣之心,王翦杀人灭口,恶人告状。”“那依吕叔之见,应该如何呢?”“自然是遣人入齐,面见王翦,等人回来再定诸事。”嬴成蟜静思片刻,摇了摇头。“不必。“东海郡、琅琊郡、胶东郡、济北郡、临淄郡、会稽郡,齐地六郡兵马尽归王翦统率。“再给王翦自招兵马之权,上数不计,便宜行事。”吕不韦豁然变色。“胡闹!齐地当初就没有遭受兵乱,若是王翦意欲谋反,以他带六十万秦兵踏破楚国之能,攻破函谷只在数年之间!“其子王贲坐镇东北,三番五次上表,意欲征讨东胡。若是这父子二人联手,以王贲统率的东北边军加上齐地兵马……”吕不韦倒吸一口凉气,说的自己都害怕了。大秦帝国最能打的人,不是如今声名鹊起的西北蒙恬,而是王翦、王贲两父子。六国之中,五国都是这两父子所灭,大秦帝国唯一的一家一门双侯!嬴成蟜却没有露出一丝半点的恐惧之色,面色平淡。“我们拦得住嘛?“吕叔应该最清楚,齐地那边有多少反叛势力蠢蠢欲动,或者是已动。“田横、田儋、田荣三兄弟复齐旗号马上就打起来,张良一心兴复的韩国也将借齐地还魂。“还有长年追查不到的项氏一族,齐楚两地游动频繁。“吕叔,你说,我们怎么拦?“皇兄身死,这天下必然大乱,拦不住。”吕不韦恨恨地骂了一句这嬴政死的真不是时候,然后还是坚决反对。反对理由很简单,这些所有的反叛势力加起来都没有一个王翦吓人。就算知道有李牧、廉颇两员名将,吕不韦也不想给王翦机会。“隆冬时节,无法远征。“与其让那些六国余孽兴盛壮大,不如信任王翦,兵马只有那么多,王翦招的多,六国余孽就招的少。“远水解不了近火,让那些只惧怕皇兄的六国余孽,见识一下武城侯的锋芒罢。齐人没有流过血,这次补上。“就这么定了,写回书罢。”吕不韦按着左胸,其内有一颗扑通扑通,跳速越来越快的心脏。“若是王翦聚拢齐人西进,直逼函谷怎么办?”嬴成蟜回道:“若真是如此,齐地那些七七八八难以数清的六国余孽,不是被王翦消灭,就是被王翦收到帐下,到时候正好一举灭之。”吕不韦加重语气,深刻提醒。“我不知道你的自信是来自李牧,还是来自廉颇,亦或是蒙恬。,!“但兵无常势,水无常形。“面对王翦,谁都不敢说必胜,何况还有一个王贲。“李牧胜过是占了守城的便宜,二者互换,他可敢言能下王翦之城?”嬴成蟜摊开双手。“你看,我下决定你又不遵,还要找我来多做事,你这不是架空我嘛?”吕不韦深吸一口气,恨恨地道:“我只是不想死后见你阿父的时候,无颜面对之!”说着话,摊开一张黄纸,在上按照嬴成蟜的意思给武城侯回文。该说的他都已经说了,既然成为秦王的小秦王仍然固执己见,那他只有支持。他相信嬴成蟜,从那个孩童弹琉璃球的那天开始就相信了。“你最近杀心过于重了。“你是不是忘了,你自西北归来,你一路嚣张跋扈,就是为了少杀些人。”嬴成蟜四仰八叉地躺下,闭上双眼。“那些人该死,早二十年就该死了。“兼并土地,逼良为娼,把人逼到绝路,再以一斤粟米签下其人,收为隶臣妾……“他们人头的唯一作用,就是帮助我恐吓住群臣。”毛笔在纸张上书写不断,吕不韦有些担忧。“我怕你杀不住手。“从前你不会说齐人没有流过血,这次补上这种话。“对生命要有敬畏,这是你自己说的。“你现在当了王,虽然做的事还是为民,但好像民的地位在你心中低了许多。”许久,没有等到嬴成蟜回应,吕不韦便住嘴不言,一直笔耕不辍。直到写完,他才转头去看嬴成蟜,看到嬴成蟜胳膊放在眼睛上,呼吸平稳,似已睡去。老人叹了口气。韩地的事,是他一生的痛,摆满他屋子的那些牌位,每次都会让他的心如针扎一般,他不希望嬴成蟜晚年也是如此。行差踏错一步,后半生都会伴随悔恨。“吕叔,你相信我嘛?”吕不韦失笑。“我若不信你,会替你代笔写这封回书?会按照你的吩咐做计划实施?”嬴成蟜一句废除隶臣妾说的轻松,但怎么废除呢?所有世家把隶臣妾都放出来?那放出来的隶臣妾怎么安置呢?这些具体步骤,都要吕不韦打点。:()吾弟大秦第一纨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