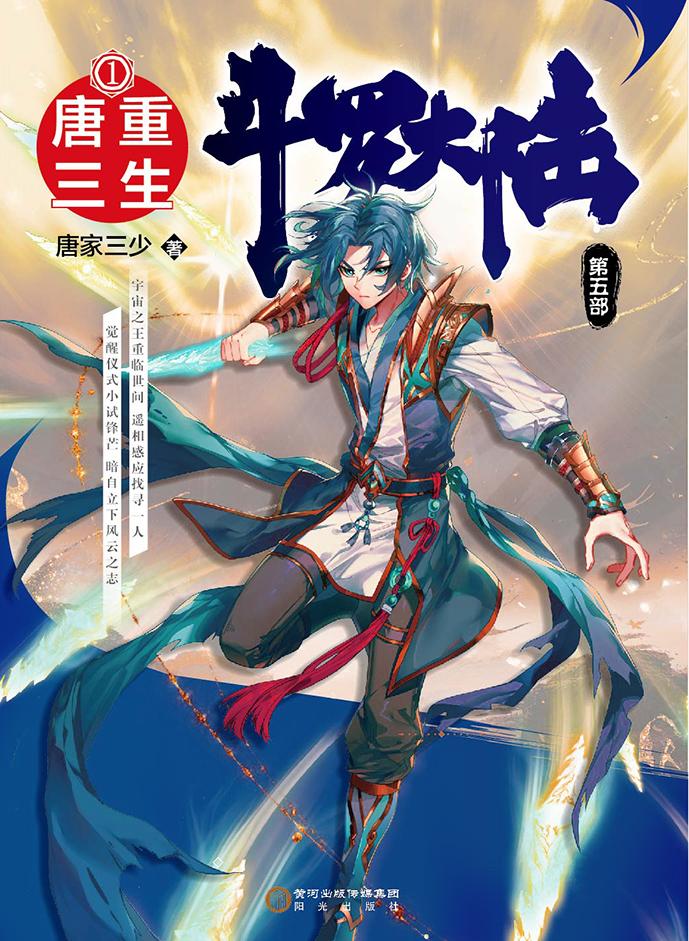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作精捞男丢球跑了 > 大起大落(第1页)
大起大落(第1页)
时钦双手哆嗦着把所有口袋扯出来抖了又抖,还是空的!
他连滚带爬摔下床,左膝盖重重磕在床沿棱角也不觉疼,弯下腰就往床底探,只有积了层厚灰的地面,和角落几个不知猴年马月扔的烟屁股。
招待所有公共淋浴间,房间不带厕所,巴掌大点地方,一眼能扫到头。他把枕头床单被褥全翻过来,抖得碎絮乱飞,连床板缝都用手指抠遍了,仍不见黄金和表的影子。鞋子里现金还在,裤兜里零碎也没丢,偏偏最值钱的家当,一夜之间全没了。
惨白的脸色没缓过来丁点,时钦全靠扶着墙才没晃倒,心脏跳得又急又乱,撞得胸口又疼又发紧,左膝盖的疼也追了上来,一抽一抽扯着神经,整个人乱了套。
明明藏得那么严实,门锁反复检查过,哪怕那破锁一拧就开,根本没人知道他揣着宝贝。
可是真的丢了……
时钦面如死灰,瘫坐在床上,嗡嗡的杂音在脑子里转,吵得他发木,绝望地想,老天又开始折磨他了,这种苦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有个头?难道本命年就活该这么倒霉吗?
凭什么啊?
他不甘心地揪紧床单,指头抠进布眼儿里,指节憋得发白。
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吵嚷,有人扯着嗓子喊“昨晚遭贼了”,时钦猛地被拉回魂,起身一把拽开门,见走廊里聚了几个汉子,正围着吵吵,大骂招待所治安差。
“他妈的,哪个畜生干的?偷俺裤衩子!”
“我保温杯也叫那畜生顺走了!”
“坏了,我晾窗户那儿的衣服咋没了?”
“这过道里没监控,怎么查啊?警察可不管这个。”
招待所是栋两层老楼改的,楼里飘着股霉味,走廊的灯忽明忽暗。老板拿着一软皮本和圆珠笔,挨个敲门问了一遍,最后统计出来,也就三个人丢了东西。
一条裤衩子、一个保温杯,还有件晾在走廊通风口的衣服。
时钦在旁边从头到尾盯着情况,就见老板跟那三个汉子摆手,语气很敷衍:“算了算了,几样不值钱的东西,犯不着把警察折腾过来。”转头给他们各免一天房费。
其中一汉子登时急眼,拍着墙喊:“那衣服是我正经二百多买的,才穿了没几天!”他嚷得脸红脖子粗,非讨个说法,老板被他唬住,这才不情不愿松口,多给免了两天。
一场风波就这么轻飘飘过去了。
时钦最怕的就是警察,更不敢报警。等看热闹的人三三两两散了,他才匆匆下楼,脚步都有些发虚,心里还抱着点微弱的希望:万一是招待所里的内贼,跟老板多打听两句,没准能有线索。
可老板看见他,直接就没给他好脸色,问他:“你也丢东西了?”
时钦连忙点头,刚要开口,老板却不耐烦地挥挥手,赶苍蝇似的:“给你免一天房费,甭跟我烦了啊,不乐意报警去,一天才挣你们几个钱,亏姥姥家去了!”
就免四十块钱的房费……
时钦咬着后槽牙,鼻腔蓦地冲上一股酸意。最早以前睡桥洞,裹着破麻袋当被子,被蚊虫咬到浑身是包的苦日子都熬了过来,他总觉得没什么扛不过去,只要有一口气在。可这会儿胸口像压着巨石,沉得他喘不上气,怎么都扛不住。
他终于懂了,为什么一根草就能把骆驼压死。
昨天在颠簸的车里,他还捂着内袋偷偷高兴来着,等把黄金变现,就想办法租个带窗、有卫生间的小屋,干脆租到过年,不用再四处找活儿干,每天睡醒了看看电视,晚上自己学着做做饭。他以为日子总算能好起来,能顿顿吃上肉,慢慢把烟戒掉。
现在,什么盼头都没了。
时钦死死掐着掌心,指甲几乎陷进皮肉里,尖锐的痛感逼着他把腰杆再挺直一点,绝不能在外人面前丢脸。可心里的委屈瞬间涨满了胸腔,为什么谁都可以踩他头上拉屎撒尿?他视线一下子模糊,滚烫的液体不听使唤,砸了下来。
“哎哎哎,你哭啥!”老板叫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