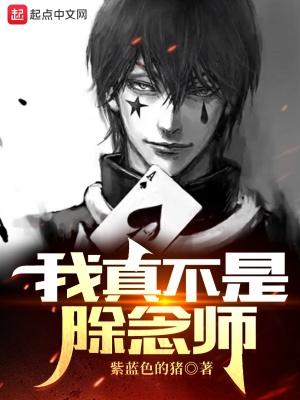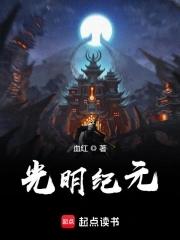马羊小说>离婚律师他送我玫瑰 > 文吉独白 我曾拥有终归赤贫(第2页)
文吉独白 我曾拥有终归赤贫(第2页)
(周五上午,律所,决绝的归还与无力的反击)
周五上午,我搭乘最早的航班,带着一身隔夜的酒气、彻夜的疲惫,以及那份被李笑然的诀别信刺穿后仍在隐隐作痛的不甘,降落在上海虹桥。几乎是一路疾驰,催促着司机,近乎失态地冲回了律所。
电梯直达20楼,步履生风地穿过尚显冷清的开放式办公区,面对助理小杨那句“文律早”的问候,我几乎无心回应,只是径直推开了自己办公室那扇厚重的木门。
近午的阳光透过百叶窗,在光洁的地板上投下平行的光带。办公室里空荡而寂静,与窗外都市逐渐鼎沸的声浪仅一窗之隔。那个牛皮纸文件袋,如同一个等待已久的判官,在我开阔的桌面上显得格外突兀,成为这方空间里唯一的焦点。
目光第一时间锁定其上——小杨果然专业且拎得清。袋子是反过来扣在桌面上的。印有李笑然个人信息和邮戳的、那令人心绪不宁的正面,被妥帖地隐藏了起来。这个细节让我紧绷的神经略微松弛了一毫米,至少,我不必在助理面前立刻面对那行宣告终结的地址。暴露在阳光下的,是牛皮纸文件袋相对干净的背面。
我随手将公文包搁在沙发上,甚至没心思脱下西装外套,便几步跨到办公桌前。我的目光,急切地落在了那背面上。
那里,用蓝黑墨水,写着一行端正中透出几分学生气的字迹,每一笔都带着郑重的顿挫,仿佛要将所有的恳切都凝在笔尖:
「快递员哥哥辛苦了!」
一瞬间,时光倒流,万物凝滞。我仿佛被定在原地,所有奔波的燥热、所有预设的防备,都在这一刻冰消瓦解。
随即,一股复杂的、难以名状的情绪涌起,我竟然……控制不住地,从喉咙里滚出一声极轻的、气音般的笑。那不是欢愉,是跨越十四年光阴,被那个小心翼翼、连称呼都怕冒犯、只盼心意速达的纯真少年迎面撞上时,产生的巨大荒谬感和无法排遣的酸涩。那个十八岁的我,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郑重,希望快递员能善待这份承载了自己全部悸动的信件。
这质朴得近乎笨拙的善意,像一面纤尘不染的镜子,瞬间照见了我的不堪与算计。笑容极快地从嘴角隐去,如同被风吹灭的烛火,留下更深的静默。那行字,无声地丈量出了十四年的沟壑。
我伸出手,指尖似乎还带着奔波的微尘,轻轻地将牛皮纸文件袋翻转过来。
现在,我必须面对它了。我坐下来,将自己沉入宽大的皮椅。办公室里有些憋闷,混合着昨日残留的淡香和此刻独属于我的焦灼。几乎是生理性地,我感到急需尼古丁的安抚。我起身,用力推开身后那扇厚重的玻璃窗。
20楼的风立刻蛮横地涌入,带着都市高空特有的、剥离情感的冷硬。窗外,是淮海中路密不透风的钢铁丛林,玻璃幕墙相互反射着冷冽的阳光,构成一片规整而疏离的天际线。这里寸土寸金,律所租下这片临窗的合伙人办公室,更多是一种身份的象征,至于通风、采光是否宜人,根本没人在意。大部分合伙人如同候鸟,不是在出差,便是在会议室里征战,这方寸之地,不过是个人生战场里一个名义上的据点。恐怕整层楼,也只有我还会保留着抽烟的习惯。
我点燃一支烟,深深吸了一口,让那熟悉的灼热感熨帖着空洞的胸腔,然后才重新坐定,将目光投回桌上那个牛皮纸文件袋。
正面,是那熟悉的、当年写得一丝不苟、甚至带着几分刻意雕琢的字迹,熟悉的邮戳,以及……那依然敞开着、仿佛无声嘲弄的封口。她连最后一丝形式上的挽留都吝于给予。彻底地,归还。
烟雾在指间升腾,我看着那袋子。如今除了签署重要文件或偶尔在证据上画个圈,几乎不再动笔。那支价值不菲的万宝龙传承系列钢笔,更多时候是西装内袋里的一件道具,象征着阶层,而非情感的载体。而眼前这纸上十四年前的笔迹,却如此沉重,仿佛凝结了那个年纪所有的赤诚与忐忑。
我小心翼翼地,像对待一件易碎的出土文物,指尖慢慢探入袋内,触到那叠熟悉的、带着岁月干爽气息的信纸。
里面,安放着我十四年前写的那四封信。除此之外,空无一物。没有任何额外的字条,连一道铅笔的划痕都没有。利落得像一场外科手术,精准地切除了所有回旋的余地。
我将它们逐一取出,摊开在漫溢着阳光的桌面上。然后,我拿起了最上面那一封。
信纸被仔细地折成了飞机的形状——这分明是当年我自己寄出时的手笔。这个发现像一根细针,猝不及防地刺入我心口最柔软处。《小王子》里,飞机是连接飞行员与玫瑰的孤独旅程,是沙漠中意外降落的开始。那个十八岁的我,是怀着怎样郑重又浪漫的心思,在将信纸塞入信封前,赋予了它飞向你的姿态?此刻,我必须极其耐心地,一点点展开那些脆弱的折痕,仿佛在试图抚平岁月在我心上刻下的褶皱。
信纸已经泛黄,散发着旧纸张特有的、淡淡的被岁月侵蚀的气息。上面那个少年青涩而真诚、带着些许忧郁的笔迹,谈论着梦想、孤独、对未来的不确定,还有……那些曾被我视为不堪的脆弱、如今看来却无比珍贵的赤诚。
其中一封,甚至是用英文写就的。那时我是市重点的尖子生,经常参加英语竞赛,虽曾在一次关键的市赛中折戟,但内心那份想要在她面前展示最好一面的冲动,促使我提笔用另一种语言,试图构建一个更富哲学意味、更显成熟的形象。我写道:
“Soonerorlater,wemustrealizethereisnostation,nooneplacetoarriveatondforall。Thetruejoyoflifeisthetrip。Thestationisonlyadream。Itstantlyoutdistancesus。”
(迟早,我们必须明白,人生没有终点站,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一劳永逸地抵达。生命中真正的快乐在于旅程。终点站只是一个梦。它总是在前方,与我们保持距离。)
“Itisnttheburdensoftodaythatdrivemenmad。Itistheregretsoveryesterdayandthefearoftomorrretandfeararetwinthieveswhorobusoftoday。”
(并非今日的重负让人疯狂,而是对昨日的悔恨与对明日的恐惧。悔恨与恐惧是一对孪生窃贼,偷走了我们的今天。)
“Sostoppagtheaislesandtingthemiles。Instead,climbmoremountaimoreicecream,gobarefootmoreoften,swimmorerivers,watchmoresus,laughmore,cryless。Lifemustbelivedaswegoalong。Thestationwillesoonenough。”
(所以,停止在过道里踱步,停止计算里程。相反,去爬更多的山,吃更多的冰淇淋,更常赤脚行走,在更多的河流中游泳,看更多的日落,多笑笑,少哭泣。生活必须在行进中体验。终点站自会很快到达。)
烟雾在眼前缭绕盘旋,将泛黄信纸上的字迹晕染成一片模糊的过往。我夹着烟的手指悬在桌沿外侧,仿佛那点微点的火星真会点燃什么——不仅是这些脆弱的纸张,更是那个曾写下这些句子的、十八岁的自己。
多么讽刺啊。这流畅优美的英文句子,此刻读来像极了一场精心排演的独白。每一个劝人"享受旅程"的单词,都在嘲笑我此刻的惶惑不安;每一句告诫"停止恐惧"的短语,都在映照我这些天的患得患失。
原来我始终被困在这条过道里。
从周三那个震动开始,我就在心里来回踱步,计算着每一个可能的里程——该如何回应,该如何试探,该如何挽回。我像个精明的商人,在情感的账簿上反复核算,却忘了最重要的事:真诚地面对这一刻,面对她。
而她早已抵达了我永远到不了的站台。
那个写下"山河浩荡,在此作别"的李笑然,才是真正读懂生活的人。她预见了所有美好背后的泪水,却依然选择真诚地前往,然后坦然地告别。她活成了这些英文句子本该指引的方向,而我,不过是个在原地打转的囚徒。
多么可笑。
三十多岁的文吉,穿着高级定制的西装,用着万宝龙钢笔,看似拥有一切,实则一无所有。而那个十八岁的少年,至少还拥有李笑然,还拥有诚实面对内心的勇气。
窗外的风裹挟着八月底的暑热掠过耳畔,指尖抚过信纸上微微凹陷的笔迹。那些蓝黑墨水写就的字迹仿佛突然变得滚烫——
我看见了。看见那个穿着校服的少年,就着昏黄的灯光小心翼翼地折着纸飞机;看见他在信封上写下"快递员哥哥辛苦了"时,脸上那份虔诚的郑重;看见他把《小王子》装进牛皮纸袋时,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。那些被我刻意遗忘的细节,此刻如潮水般涌来,将我彻底淹没。。。